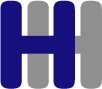[摘 要]流域水環境保護執法面臨“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本位主義”的雙重挑戰。因此,流域水環境保護執法改革的核心是重塑統一、高效的流域水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體制及相應的法律框架。結合國際經驗和國內地方性試驗,可資借鑒的改革選項包括建立流域統一監管和綜合執法機構、構建跨地區和跨部門的多樣性的聯合執法協作機制、組建環境警察以及激活社會力量參與流域執法監督等。
[關鍵詞]綜合執法;聯合執法;流域;水環境保護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嚴峻的水污染問題為治國與治水的古老智慧嵌入了水環境保護的新元素。“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詮釋了水資源和水利在傳統國家治理中的地位。污染問題導致的水質性缺水、水環境容量超限以及水生態受損,凸顯水資源、水環境和水生態“三位一體”的依存關系。如是,流域水資源、水環境和水生態綜合管理成為現代國家治理的重要領域。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出臺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水十條”)、修訂《環保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從法律制度層面加強流域水環境保護。黨的十九大深刻認識到“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提出“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實現水環境質量改善的目標必須整合流域水環境管理體制并優化配套管理政策。其中,關鍵是重塑統一、高效的流域水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體制及配套法律政策框架。
一、流域水環境保護執法面臨的現實問題
流域水環境保護執法涉及“上下游、左右岸”不同行政轄區以及“水資源、水環境和水生態”不同職能部門之間的關系。以屬地管理和部門管理為基礎的水環境行政執法體制很難兼顧流域的整體性和系統性要求,面臨“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本位主義”雙重挑戰。
首先,地區間執法標準差異和部門間法律法規沖突制約流域水環境保護執法的協同性和有效性。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和環境執法能力不同,流域“上下游、左右岸”不同轄區甚至同一轄區內部執法標準和規范化程度都會存在較大差異。以珠江流域為例,珠三角經濟發展水平、環境標準和規范化程度較高,對陶瓷加工等污染產業的嚴格執法導致污染產業向粵西的肇慶和上游湘贛等省轉移。上游地區的污染物最終還是會隨地表徑流帶回下游地區,流域污染的范圍反而更大。另一方面,水資源、水環境和水生態的功能和用途管制差異,相關職能部門劃定的功能區劃和管理標準不同甚至相互“打架”。以功能區劃為例,環保部門依照《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劃定水環境功能區劃,水利部門依照《水法》劃定水功能區劃。二者均有上位法支撐,環保和水利部門在流域執法過程中都側重執行本部門制定的政策規章和行業標準,而分散的劃分標準不利于水環境、水資源和水生態整體銜接。
其次,流域涉水職能部門過多、執法體制過度分散切割流域水環境保護的整體性并且加劇相關部門職責模糊程度。一方面,流域涉水職能部門過多,流域執法體制過度分散化和碎片化,切割流域水環境保護的整體性和系統性要求。《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條規定,環保部門對水污染防治實施統一監督管理。交通部門的海事管理機構對船舶污染水域的防治實施監督管理。縣級以上水行政、國土資源、衛生、建設、農業、漁業等部門以及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水資源保護機構,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對有關水污染防治實施監督管理。從污染源到入河排污過程中,農業和農村面源污染、河岸濕地保護、污水處理廠和管網設置、水土流失和入河排污口設置等分屬農業、林業、建設、水利等部門,環保部門的統一監管職責缺乏完整職能和必要手段。另一方面,職能部門過多和“九龍治水”進一步模糊流域水環境保護執法主體權責,導致經常性的相互推諉。根據《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八條的規定,造成漁業污染事故或者漁業船舶造成水污染事故的,由漁業主管部門調查處理;其他船舶造成水污染事故的,由海事管理機構調查處理;造成漁業損害的,漁業主管部門參與調查處理。由于現實中漁業污染事故原因較多,監管執法過程中往往難以確定執法主體、問責對象和賠償等,加劇相關職能部門推諉扯皮。
再次,流域屬地執法事權配置無法實現“督企”與“督政”的激勵兼容,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流域水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在國家監察、地方監管和單位負責的環境監管體制框架下,流域屬地執法針對企業和點源污染,無法實現“督企”與“督政”的激勵兼容。一方面,單靠監管點源違法行為無法統籌解決流域水環境保護相關的飲用水源地、農業面源污染、河道非法采砂等系統性問題。另一方面,流域水環境污染的根源是產業結構不合理、地方保護主義等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結構性矛盾。在流域國家監察不到位的情況下,無法實現有效“督政”的目標和從根本上提高流域水環境執法的有效性。
二、流域水環境保護執法的國際國內經驗
流域水環境保護執法的國際經驗和國內示范區的改革探索集中體現在:建立流域水環境管理機構整合水環境監管執法職責、構建流域跨地區和跨部門多樣性的聯合執法協作機制、組建具有環境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權的環境警察,以及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在流域執法監督中的作用。
(一)建立專門的流域水環境管理機構,整合流域水環境監管執法職責
“二戰”以后,由于水質和水環境問題受到關注,發達國家意識到水資源和水環境的相互依存關系,將流域水環境管理職責向中央或聯邦政府轉移、向環保部門集中,在流域管理上實行水質和水量統一管理。以美國流域水環境保護為例,1936年特拉華、新澤西、紐約和賓夕法尼亞州以自愿州際合作方式建立松散的特拉華河流域州際委員會,包括處理水質問題(由四個州的衛生局代表組成)和水量問題兩個小組委員會,實現水質和水量統一管理。1961年建立了聯邦-州際特拉華河流域委員會,委員會由四個成員州州長和代表美國總統的內政部部長組成。該委員會被賦予了極大的權力,直接建立各種影響流域內水質和水量(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措施,包括調節流量以便調節水質、控制和減輕現有的污染、實施有效的流域管理(防止土壤侵蝕和促進土地開墾)和森林保護實踐,并實行漁業和野生動植物保護措施、調節和控制流域的抽水量和分流量等。[1]
國內遼河流域干流、“兩湖一庫”積極探索試驗流域綜合管理和綜合執法體制改革。2010年遼寧省政府組建參照公務員管理的直屬事業單位遼河保護區管理局,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遼寧省遼河保護區條例》第八條規定:“省遼河保護區管理機構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規定,統一負責遼河保護區內的污染防治、資源保護和生態建設等管理工作,履行水利、環保、國土資源、交通、林業、農業、漁業等有關監督管理和行政執法職責。” 2010年貴州省人大常委會通過《貴州省紅楓湖百花湖水資源環境保護條例》,明確在紅楓湖、百花湖兩個飲用水源地建立“兩湖”管理局(后將阿哈水庫納入,簡稱“兩湖一庫”管理局)。該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在兩湖管理機構管理范圍內有關兩湖水資源環境保護的環保、規劃、水利、林業、綠化、建設、農業、衛生等方面行政處罰,由兩湖管理機構實施。”
(二)構建流域內跨地區和跨部門的多樣性聯合執法協作機制
流域水環境保護執法需要地區間和部門間的合作,構建跨地區、跨部門多樣性的執法協作體系是流域執法管理方式創新的重要舉措。
以美國流域執法為例,主要是通過州環境委員會、環境正義維護機制和部門間諒解備忘錄等實現跨地區跨部門執法協作。首先,1993年美國20多個州環保局長自發建立非官方非營利的州環境委員會以加強州際環境執法協作。州環境委員會下設執行委員會和常設專業委員會。其中,專門委員會包括水委員會、大氣委員會、廢物委員會、跨介質污染物委員會、規劃和守法委員會,以及工作組和論壇等臨時性機構。[2]其二,1994年美國環保署牽頭創建“聯邦機構間環境正義工作組”,以加強部門之間的政策協同和執法協作。該工作組的職責包括與聯邦機構合作,為其提供指導并作為信息交換中心,制定環境正義戰略,確保其項目、行動和政策的連續性;支持聯邦機構合作收集數據;開發聯邦機構之間合作的跨部門環境正義示范工程等。[3]其三,美國環保署與內政部、農業部等部門協調,簽訂諒解備忘錄達成協調管理和執法的共同協議,解決跨部門管理和跨要素的環境違法案件;協調部門間守法援助事項,共同跟蹤各類援助活動,測量援助效果。
國內一些流域也自主探索建立了一系列的跨地區、跨部門聯合執法協作機制。例如,2012年太湖流域的浙江省嘉興市秀洲區和江蘇省吳江市環保局建立邊界區域環境聯合執法工作機制,嚴厲查處邊界毗鄰區域的環境違法行為等。2013年貴州省遵義市和四川省瀘州市環保局簽訂《赤水河流域環境保護聯動協議》,每年開展兩次以上跨市界斷面和分水線聯防聯控、重點污染源聯合交叉執法檢查、跨區域環境違法行為聯合查處等。
(三)組建環境警察以提高流域水環境保護執法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設立環境警察、生態警察或類似警種承擔環境違法犯罪執法權和偵查權。其中,德國的環境警察最有代表性。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護、建設與核安全部主管環境保護外,在聯邦內政部還設有環境司和專門的環境警察。[4]德國聯邦環境警察的職責范圍包括環境違法與犯罪的預防、自然保護區的監管、環境保護行政部門執法人員的安全保障等。在流域水環境保護方面,聯邦環境警察主要通過巡邏和遙測工具檢查污染情況,一旦發現污染,環境警察有權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將污染控制在最小范圍。[5]此外,德國境內水系發達、水路眾多,設有專門的聯邦水上警察管轄監管可通航水路或其他可通航水體河流、湖泊船只質量和安全,承擔水質的協助監管工作,處理水體環境污染和水上交通事故。[6]易比河、萊茵河和多瑙河都有水上警察。
國內環境和資源保護主要由警察機構內多個警種分別行使,警察環境管理職能處于相對分散的狀態。例如,公安部門的刑事警察負責打擊破壞環境資源的犯罪活動,治安警察負責廢品回收業管理和危險化學品管理等,交通警察負責機動車大氣污染管理,林業部門的森林警察負責森林和野生動植物保護。國內個別流域因應環境保護的現實需要,探索建立了環境警察。例如,昆明市公安局環保分局與水務治安分局合并組建水上治安分局,開展打擊污染破壞環境、醫療廢棄物安全、高污染燃料禁燃等專項行動。2010年遼寧建立省公安廳直屬的遼河保護區公安局,實行人事上以公安廳為主、業務上以省遼河保護區管理局為主的雙重管理體制。遼河保護區公安局行使市級公安機關的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權,主要職責是維護保護區內治安秩序;預防、制止和懲治涉及危害保護區治理和保護的違法犯罪活動;保障遼河保護區管理局行政執法。
(四)積極發揮社會力量參與流域水環境保護日常執法監督
政府無疑在流域水環境保護中起主導作用,但個人、家庭和社會組織參與在流域日常監督中也是不可忽略的。20世紀90年代起,德國柏林的市政部門提出將河流承包給附近居民的政策,河流周邊環境得到持續性改善。[7]居民與河流管理部門簽訂合約自愿承包河流,確定承包長度和時間期限。承包者有權接受培訓以明確“承包”河流的職責,學習水質檢測的簡易技術和如何監管好河流。承包者的義務包括查看承包河段是否泛起泡沫、有無魚類死亡、是否有家庭向河流傾倒生活垃圾等。如果發現水污染問題和違法情況,立即向環境警察報告,彌補環境警察信息不對稱,以減少人員需求和降低政府成本。政府以減稅和免除部分市政管理費作為常態激勵。
三、流域水環境保護執法體制改革、管理變革及相關建議
流域水環境保護執法改革關鍵在于回應屬地執法和部門執法體制導致的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本位主義難題。結合水污染防治法和流域管理體制改革,未來需要進一步結合國際國內經驗,重塑統一高效的流域水環境監管執法體制和完善相關配套政策。
(一)探索整合涉水部門執法職責,建立流域統一監管和綜合執法機構
《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條延續了環保部門統一監督管理;海事機構對船舶污染專項監督管理;有關部門和流域機構協同監管的水環境監督管理的體制。因此,職責交叉和“多龍治水”的現狀與水環境監督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仍然有一定的距離。法律中有關監督管理體制的規定,建立在國務院機構改革成果基礎上。水環境監督管理體制將隨著進一步的改革而得到不斷豐富和補充。[8]
根據美國流域水環境水資源綜合管理和國內遼河流域、“兩湖一庫”管理局的成功經驗,探索整合環保、水利、農業、林業、建設等部門涉水監管職責,構建流域水資源、水環境和水生態統一監管和綜合執法機構,最大限度減少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本位主義對流域監管執法的掣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32次會議明確按照流域設置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機構,以遵循生態系統整體性、系統性及其內在規律。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可以優先在水環境保護問題突出的流域開展流域管理體制改革試點。同時,建議在流域水環境保護統一監管和綜合執法機構尚未實現前,賦予環保部區域環境保護督查中心的行政機構主體資格,改變目前的委托執法和參公管理事業單位法律地位,發揮其在流域水環境保護中“督政”和跨地區協調中的積極作用。
(二)構建流域跨地區、跨部門的多樣性的聯合執法協作機制
《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條明確建立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水環境保護聯合協調機制,實行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監測、統一的防治措施。具體到流域水環境保護執法方面,應該以流域為單元,制定統一的環境執法標準。建議在環境問題突出的流域和面積相對較小的流域試點流域上下游、左右岸的統一環境執法標準。通過統一環境執法標準,防止因缺乏流域執法的整體意識導致的污染轉移問題。
以此為基礎,構建流域內跨地區和跨部門的多樣性的執法協作機制。環保部、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已經聯合制定了環境保護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工作辦法。具體的制度設計包括案件移送、證據收集和使用、協作機制的形式、信息共享等。[9]鑒于流域水環境保護執法的復雜性,建議流域內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之間通過自主簽訂跨地區、跨部門的聯合執法協作協議,將交叉執法、邊界執法等制度化和常態化,將聯席會議、定期會商、信息通報和共享、聯合執法等予以制度化和規范化。
(三)設立環境警察提高流域水環境保護執法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環保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環境保護的法律已經完成修訂,人民警察法正在修訂。建議以《人民警察法》修訂為契機,明確設立獨立的環境警察警種,賦予環境警察開展環境違法和環境犯罪行為的治安管理和刑事執法權。短期內,優先賦予水上公安等警察流域水環境保護行政執法權和偵查權。長期看,在不增加警察編制情況下,擴充其在水資源、水環境和水生態保護領域的監管執法職能。鑒于環境警察的專業性和技術性要求,建議環境警察實行環保部門和公安部門雙重管理,人事上以公安部門為主,業務上以環保部門為主。
(四)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流域水環境保護日常監督和執法
環保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是環境保護的重要社會力量。《環保法》和環境保護公眾參與辦法等法律法規為社會力量參與環境保護提供了制度空間。具體到流域水環境保護領域,可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鼓勵社會力量自愿簽訂協議參與流域水環境保護的日常監督和執法。水污染防治法明確省市縣鄉建立河長制,由同級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分別擔任河長,以此強化黨政領導對水污染防治和水環境治理的責任。結合國際和國內經驗,在日常監督中,可以引入“民間河長”和“承包制”作為補充,創新政府購買服務途徑,充分激發社會力量在流域水環境保護中的活力。
參考文獻
[1]克尼斯·鮑威爾。水質管理:經濟·技術·制度[M].北京:三聯書店,1996:312-315.
[2][3]張建宇,嚴厚福,秦虎。美國環境執法案例精編[M].北京:中國環境出版社,2013:32-33.
[4]公安部外事局,公安部人事訓練局,公安部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歐洲主要國家警察概況[M].北京:群眾出版社,2003:4-5.
[5]邢捷。論我國環境警察制度的構建[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
[6]熊琦。德國警察制度簡析[J].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06(6)。
[7]禹艷。德國的“河流家庭承包制”[J].環境保護與循環經濟,2015(7)。
[8]陸浩。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解讀[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34-35.
[9]環境保護部環境監察局,最高人民檢察院偵查監督廳,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環境污染犯罪司法解釋圖解案例手冊[M].北京:中國環境出版社,2017:86-95.
[基金項目]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國家和流域水環境保護法律制度創新及其示范研究”(2013ZX07602-002)。
[作者簡介]楊志云,北京科技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殷培紅,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法規與體制改革部主任、研究員。